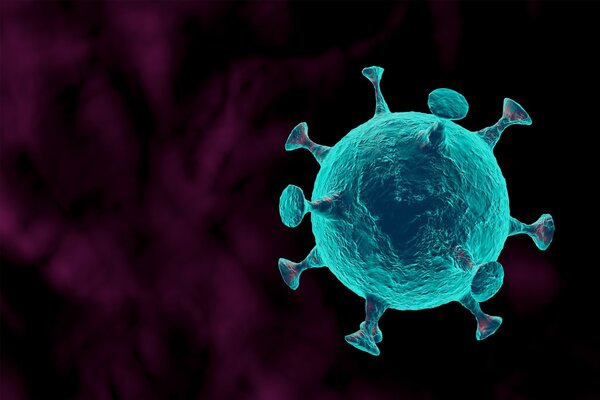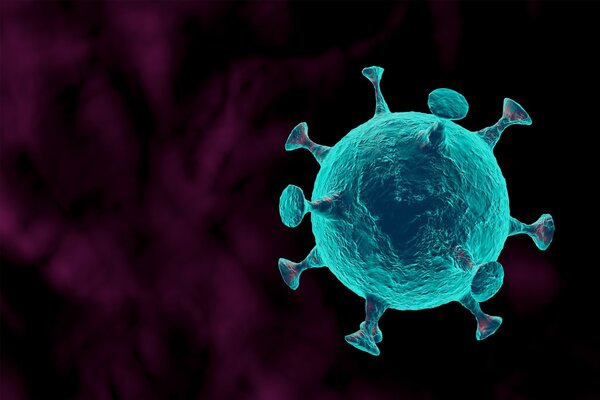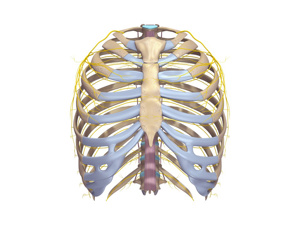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
“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这是张仲景为后人创立的治“坏病”的治则(注:现行很多书籍,此句中的“症”多为“证”。二者的区别详见后文)。而时下也有一种思潮很流行,即重视“方症对应”、“方病对应”等,关注方药超过了对人与病的关注。
这种思潮的直接影响,就是“随症治之”,对症候群用方被现在很多中医学子、甚至中医学者误认为是中医“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但这是对中医“临症察机”、“见病知源”、“治病求本”主流和正确思维的歪曲和误解,需要警惕。
是“随症治之”而非“随证治之”
理解古人 先还文字原貌
笔者认为,在刻意抬高“随症治之”的过程中,有一个桥梁——辨证论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学者先假定了辨证论治的公理地位,然后在《伤寒论》中寻找理论依据,于是“随症治之”便被选中,并命名为“随证治之”。
如果辨证论治不再拥有公理的地位,那么对“随证治之”的误解便容易得到纠正。如果古人并没有本质的、概括层面的“证”的概念,我们就应该还原古人本义的文字。只有还原了古人文章中的关键文字,我们才有可能更准确地理解古人所要表达的涵义。
有学者认为,文字的问题,不必太认真,只要在当今中医界形成共识,相互讨论时可以明白对方在说什么就可以了。
问题是中医历来强调“读经典”,读经典首先要做的就是读懂经典,如果文字的古今变迁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就需要引起格外重视。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今人之间的交流,而是与古人之间的交流。《论语·子路篇》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因此,关于“证”的“正名”问题,不可忽视。
症与证的渊源
《汉语大字典》释“症”曰:“病象。有时也泛指疾病。也作‘證’。”而对“證”、“証”、“证”的解释则分别是:“證,病症。后作‘症’。”“証,同‘證’。”“证,‘證’的简化字。”由此可知:古代的“证”即现代的“症”,两者并没有实质的区别。也就是说,在古书中见到“证”,可以直接改为“症”。这样做,更利于读懂古医书。
现代意义“证”的概念,历史究竟有多长?“证”和“症”有了明确区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现代意义“证”的历史,不超过60年。最初提出“证”,是为了强调中医学的“特色”和“优势”,是一种规定或者约定,“不仅同传统中医学固有的概念和特点相抵触,而且违背了语言学的规律。”
证、症的强行区分,发端于西学东渐之后,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谈“证”这个具有特定时代意义的概念,我们应该明白一个前提:目前习以为常、约定俗成的“中医基础理论学科”,是近代中医学界为沟通中西,适应时代潮流,以西医学为参照系,在“科学”化的背景下,将中医学中的某些固有内容作另行规定的产物。“证”的概念即其一。
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所著的《回归中医——对中医基础理论的重新认识》一书认为,“证”作为一个固定概念出现,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二版中医学院教材编写之时”,并推测这样做是为了“尽量使中医基础理论沾染上‘辩证唯物论’色彩的缘故。”
当前,如何评价辨证论治的历史功过需要另当别论,我们可以直接去做的,就是在读古书时见到“证”,可直接改为“症”。“随证治之”既然出现于《伤寒论》,直接统一为“随症治之”,当不存在异议。
“随症治之”是应急之计 并非《伤寒论》主流
《伤寒论》是将中医理法和经验方药成功结合的奠基之作,所以对中医临床影响深远,可以说是中医临床的源头和范例。
很多学者在提出自己观点的时候,都会在《伤寒论》中找依据。不过在更早的时候就有学者提醒,各取所需、断章取义式的学习并不利于中医经典的传承。当前应该做的是“寻找本意读伤寒”的工作,尽量还原本意然后从中挖掘仲景的思想,那才是真正的善学者。
谈到“随症治之”,先不要谈它的意义如何大。而应先将之还原到仲景的文字中,先弄明白仲景的本意,在这个前提下,再去“兼听则明”。
《伤寒论》中,关于“随症治之”的直接表达和类似表达,有两处:
一处为16条:“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之也。观其脉症,知犯何逆,随症治之。”
另一处为267条:“若已吐下、发汗、温针,谵语,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将此两条合参,我们可以容易地得出:汗吐下、温针等治疗后,病不解者为“坏病”,不能再用桂枝汤、柴胡汤。该怎么办呢?应该找到治疗错误的“逆”处,做对症的处理。“汗……吐……下……温针”与“坏病”、“逆”、“(随症)治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开来看。“随症治之”只是针对大原则顾及不到,需要灵活处理的“坏病”的对症治疗,不能将它人为地抬高,成为“论治一切疾病的总方法”。所以,“随症治之”是针对“坏病”的应急对症治疗,并非《伤寒论》主流。
除了“随症治之”的对症治疗。《伤寒论》中还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一是不厌其烦的日数表述,以及整齐划一的“欲解时”,所昭示的是时空统一的中医基本原理。(六经为病位,时间和空间通过中医“人与天地相应”的系统观念,统一为一个整体,于是出现了中医的时间医学。)根据这种原理的治疗,是以人为本、奉天承运的从理治疗,很多情况可以不用药。
二是49条“表里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58条“阴阳自和者,必自愈。”59条“勿治之,得……必自愈。”71条“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93条“表里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145条“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341条“厥少热多者,其病当愈。”376条“……不可治呕,脓尽自愈。”398条“病新差,人强与谷……损谷则愈。”
《伤寒论》中如此众多“愈”的表述,提示的是可以不用药“候气来复”的自愈,以及用药要不伤人体、为自愈扫清障碍、提供条件的健康治疗。
三是《伤寒例》中讲到“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伤寒论》序中讲“平脉辨症……见病知源”。这两个“源”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是针对病因病机的综合治疗,与对症用方用药治疗有天壤之别。
以上三点,只是初探,一定有很多不全面、不准确的地方,但是中医的精髓已经有所体现,这些才是中医的主流。不识病,只求方,为“执方欲加”者或为寻找“方剂的使用证据”者,追求的是下医之道。
中医祖先对后人有治未病之病、欲病之病的更高层次的要求,《伤寒论》中已经做了很多明示。只要我们放下固执,便会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伤寒理法世界、便会更多地关注人、关注人为什么得病以及如何可以不得病。中国中医科学院仝小林教授讲过一句话:“对疾病认识和把握的程度,决定了疗效。”将关注的重点从方药上移开,落实到人和病上,笔者非常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