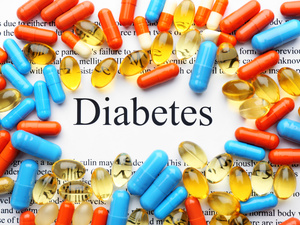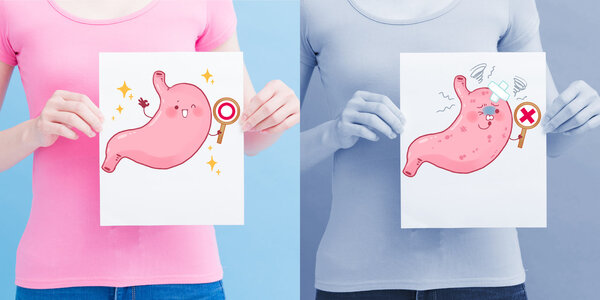出走后的自卑心理和自尊需求:陕北自古就是一块苦焦的土地,生存条件极端恶劣,自魏晋以降战乱不断;另外,陕北处于边地的边缘性和包容了他民族、他区域的生存方式后自然形成的文化维度的多向性,构筑了陕北人疏淡民族法理、放逐村落秩序的乡土消解心理与文化移植心理。“逃离”与“出走”始终是陕北人亘古难移的精神情结,也成为隐喻在区域民族灵魂深层中的精神意象,同时成为我们解读陕北文化进而诠释其生存状态的一个解码。
路遥在极度困厄中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他成绩优异,对学校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执着情绪,这一方面来自于他对知识的爱好,另一方面,在他的内心深处,还有更强烈的改善自己身份及处境的迫切需求。在路遥的大部分小说里,主人公的设置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大都是来自于农村的优秀青年,自小成绩优异、积极上进,在书本里看到了和自己生存环境迥异的外部世界,通过自身的努力,在新时代浪潮的裹挟下,毕生为进入外部世界而努力。在从农村走入城市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就是其文化身份的认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乡下人在进城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难的处境。自幼耳濡目染陕北独特的地域文化,使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深深地打上了乡村文化的烙印,在进入城市之后,面对着另一套迥然不同相异的文化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常常觉得身份错位,流露出一种强烈的自卑情绪。在路遥的笔下,我们明显地看到,自卑并没有使主人公消极颓废、一蹶不振,而是以反作用力的方式激发出人的自尊和潜能。
在路遥的小说里,主人公一直徘徊在农村和城市的罅隙,流亡在文化的断裂地带。表现在心理状态上,都有一个共同特点:自卑与自尊的相互胶着。这无疑也是路遥本人的自况。当这些主人公在外出的过程中,触碰到城市的坚硬壁垒后,他们陷入了深深的自卑情绪。而与此相对应的,浓重的自卑感激发了强烈的自尊心,表现在行为方式上,就是对城市的抗拒。《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在学校极为自卑,“虽然他在班上个子最高,但他感觉比别人都低了一头”,“而贫困又使他过分地自尊,他常常感到别人在嘲笑他的寒酸,因此对一切家境好的同学内心中都有一种变态的对立情绪。”当穿戴时髦的顾养民一边优雅地点名,一边神气地抬腕看表时,“一种无名的怒火就在胸膛里燃烧起来”,以至于点到他的时候,他故意没吭声。 基于这样的创作心理,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在行为上通常有一个固定的模式:出走――归来。在离开农村之前,他们对这块贫瘠的土地、落后的生活感到深深的厌恶。在涌入城市后,地理位置和文化习性错位,目睹城市现代化进程衍生的弊端,他们普遍对过去的乡村生活投去了深情的一瞥,在黄土地里日夜劳作的农民,充满人情味的风俗民情,时时恪守的伦理道德以及家乡人们纯良的品性,都成为他们心底挥之不去的怀恋。路遥写孙少平时,心理是复杂的,他让后来成为省委副书记兼省会市委书记的田福军的女儿、大学毕业后成为省报记者的田晓霞和孙少平真诚相爱,以田晓霞在抗洪抢险中的牺牲使他们的爱情成为终结,又让医学院大学生金秀爱上了孙少平。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煤矿工人,孙少平把爱情最后给予了他的因公牺牲了的师傅的妻子惠英。这是孙少平合乎生活逻辑的命运结局。在这里,乡村温情成为救赎出走者的终南捷径,现实的救赎被伦理的救赎取代,路遥与母体文化的无奈合辙潜在地反映了路遥内在的困惑。遗憾的是,处于“城乡交叉地”的路遥,其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在自卑与自亢的矛盾心理下创作生成的,这些有着浓郁自传色彩的小说讲述着有关出走、复归的永恒话题。[4]由此,我们也看出,陕北的山水地气给了路遥如此多的文学馈赠,但同时也给他带来沉重的文化负累。路遥得益于地域文化的滋润而蜚声国际,同时也因文化结构的过分单一以及文化情感的过度直率凸显了其创作的艰难。
综上所述,陕北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风貌、道德人情、乡规村俗以及区域性格、历史积淀等等因素共同构成了陕北地域文化内蕴,它们胶着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凝聚力量,深刻影响着作家路遥,共同塑造了他特有的创作心理机制。这一创作心理机制一旦成型、稳固,便很难更改,他缓缓渗透于作家的作品创作中,对写作的主题、人物的形象、环境的描摹以及故事发展的去向等等产生综合性的影响,它最终决定着作家为什么写、写什么,为谁写和怎样写等最根本的价值取向。